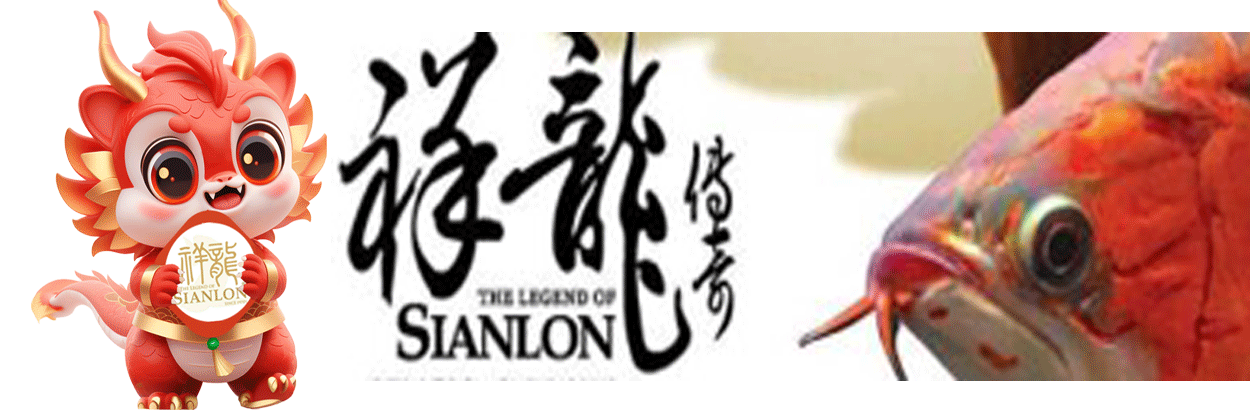金龙鱼翻白还能救吗:金龙鱼翻白肚怎样救活
的,人们都叫他“老白”,因为只是一个人过日子,所以他每年只准备了打一甑糍粑的米,当时觉得他的阻拦,是因为小气,结果,却发现自己错了, 原来,快捣好的糍粑黏性最大,手上沾点水才不至于粘到手上,如果把一双小手烤热了,再去拿糍粑,就会牢牢地黏在手上,又热又烫,我左跳右甩地也没能把那团咬手的糍粑弄掉,大伯这时端来清水,才算把我的小手解救了,末了,他还“啵、啵、啵……”
1/在郑州街头邂逅信阳糍粑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趁着周末去郑州一家较大的蔬菜批发市场置办点年货。现在购物方便,简单准备点鸡、鱼、肉、菜就行的。
没想到,在街口却有了意外惊喜——都大年腊月二十四了,还有人在郑州的街头兜售信阳糍粑。上前一打听,老人竟然是我们光山的老乡。闲聊中得知,老人和几个老乡在郑州郊外租了一处民房,常年驻扎郑州,以销售信阳糍粑为业。老几个负责在“家里”生产,他负责对外销售。老人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出摊了,明天就打道回府,准备回家过年了。
这糍粑不比年糕,年糕的材料是糯米与糙米按一定比例掺和一起在做,而糍粑的用料则全是糯米,糯米贵,所以糍粑的价格不比年糕便宜,老人的要价是六块钱一斤。我挑了一块(这玩艺不好消化,只是尝尝鲜),过秤后将近三斤,16块5毛钱,老人收了16块。
在我们老家,年关将近的味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杀年猪,另一个就是打糍粑。杀年猪的事,一个村子一年中最多有几户条件上好的人家才舍得,而打糍粑却不分贫富,家家户户都储存有几箩筐糯米用来打糍粑。

当然,我说的是六七年代的乡村,现在的乡村,年味越来越淡,已经很少有人自己在家打糍粑了。
2/渐行渐远的年味
打糍粑这活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完成得了的,得靠集体的力量。时间都选在腊月农闲时,十来户人家联合起来,今天你家,明天我家,轮流着反各家的糍粑打完了,就已近年尾了。
打糍粑并不是什么技术活,只是力气活。每轮到一处,主人家得提前一天将糯米洗净、泡发,负责烧火的人也会提前过来,将泡好的糯米装进木甑里,盖严封边,隔水大火蒸熟。
这时,男人中的壮劳力就出场了,将蒸熟的糍米饭倒入石窝,几个人操起木拐,转着圈地捣,直到糯米捣成泥状便开始翻窝(翻窝算是技术活,几个人的木拐同时举起,将糯米团抛向空中,又稳又准地落回石窝),翻窝后接着捣。
下一道工序就是用石锤(也有用木锤的)砸,一人抡锤,一人翻坨,两人要配合默契才不至于翻坨人的被锤子伤到。
待石窝里的糯米完全变成晶莹如玉的一团后,再抱到案板上整形、切块,一窝糍粑算是大功造成。
虽然只是简单劳动,但对于农人们来说,却是一个绝佳的社交平台。平时都是各奔各的穷日子,除了集体出工,都是各回各家,吃糠咽菜的苦涩都关起门来过,很难有这种天天混在一起劳动、粘在一起吃喝的机会,有精神的放松,有不经意间闹出小矛盾的和解。
所以,一进入腊月,人们的笑容都是舒展的。
3/忘不掉的童年美食
村村户户打糍粑的时候,也是小孩子们的狂欢节。那时学校一般还没放假,许多孩子都是身在课堂,心却飞回了笑语喧哗的村庄。不为别的,只为是去蹭点好吃的“点心”。
那个年代穷啊,长年累月的就稀饭咸菜,小孩子们根本不知道零售是啥。顶多,家里偶尔蒸米饭了,妈妈会在灶里多添把柴,让锅里的锅巴煎厚实点,就是绝世的美味了。
能遇到打糍粑这样的美事,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所以,放了学就往打糍粑的邻居家跑,名义上说是去看在那里帮忙的家长,其实就是奔着那点馋去的。但,脸皮还是薄,虽然看着糍粑咽着口水,也绝不会主动向人讨要。那时的我们,都是有羞涩感与廉耻心的。遇到大方的女主人,会主动从石窝里掐上一小团来,如果碰到个小气女人,一旁帮活的乡亲也不会让孩子们失望,他们会不顾小气女人的脸色,给孩子们一人掐上一团的。
至于能吃到什么“口味”的,这全靠运气。所谓的运气,就是时间点,如果放学到家恰好赶上木甑里的糯米刚蒸熟出锅,吃到嘴的就是香糯的米团;如果刚入石窝不久,米粒还没捣烂时,是软中带糯的粗糙米团,相比而言,这时的口感是最差的;最佳时机是,石窝里的糯米已完全捣成泥状,掐出一团来最适合粘糖吃的;再晚点,已经使上锤子时,就不能吃了,因为翻窝时是沾了生水的,如果真是铁了心地想吃,也有办法补救,那就是掐出一小团,拍成扁圆形的,拿灶火烤了吃,那是最香脆的。
往往,有了收获后,孩子们便又带着“美味”飞快地跑回家,家里还有少不更事鲜有出门的弟弟妹妹啊。这时,妈妈会将那团糍粑分成几小块,然后从柜子里翻出深藏不露的白砂糖,每块都粘点糖,兄妹这才分而食之。
4/四哥的一次恶作剧
当然,也会遇到恶作剧的长辈。
记得有一次,伯父家里打糍粑,我当然要跑去蹭吃了。结果被一本家哥哥给坑了。我叫他四哥,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见谁都爱开个玩笑,算盘打得精,当过村里的会计,算是远近闻名的能干人。那天我放学一到伯父家,四哥就热情地招呼我,馋了吧,一会四哥给你搞点糍粑,快去厨房把手烤热了,免得糍粑粘手上了。十来岁的孩子,肯定没他精明啊,于是乖乖地跑去灶窿把手烤热。待我回到堂屋时,一屋子的人都拿奇怪的眼神看我,感觉他们都憋着一脸的坏笑。只有大伯挡在我面前,“啵、啵……白、白……”地比划个不停。大伯是个哑巴,一辈子都一个人过,虽然常年见人都“啵、白、白、啵……”的,人们都叫他“老白”。因为只是一个人过日子,所以他每年只准备了打一甑糍粑的米,当时觉得他的阻拦,是因为小气,结果,却发现自己错了。
原来,快捣好的糍粑黏性最大,手上沾点水才不至于粘到手上,如果把一双小手烤热了,再去拿糍粑,就会牢牢地黏在手上,又热又烫,我左跳右甩地也没能把那团咬手的糍粑弄掉。大伯这时端来清水,才算把我的小手解救了。末了,他还“啵、啵、啵……”地跑到四哥跟前擂了他一拳。
其实,那时大家都没有恶意,只是乡下的生活太寂寞,一次小小的恶搞,会给人们带来些许快乐。
如今,大伯和四哥已先后作古,而曾经热闹的乡村已渐趋冷寂。
5/曾经的功臣食品
曾经,糍粑是家乡的功臣食品。
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其品质所决定的。别小看这一块方方正正的糍粑块子,它可是乡亲们赖以生存的方便食品。
首先,易储存。一是干存法,将糍粑切大小适当的方块,放阳光上爆晒脱水,放进竹篮里,挂于高处,可保经久不坏。另外是水存法,就是糍粑块放入水缸,注满清水,可以一存放了来年夏忙时节(不过,得注意时时换水,否则糍粑会变酸、变腐)。
其次,吃法花样繁多。时隔许久,仅我还能记起的吃法,已足以让我佩服我的乡亲们了——
最便捷的吃法——煮着吃。可以白水煮糍粑,熟了,加点盐或糖,就是一餐;也可以煮进白粥里,等白米粥快煮好时,将几块糍粑丢进粥锅里,只需一点的时间,糍粑就软糯可口了。这样,一碗本世不挡饱的稀饭就有了最厚重的内涵。这是最家常的,另外,奢侈点的,可以配米酒同煮,也可以煮糍粑下挂面……凡是你能想到的煮法都可以,它,本身就一百搭。
最原始的吃法——烤着吃。打完糍粑后,家家户户烤糍粑。最好的方法是,煮完饭的灶膛里的余烬,糍粑用火钳托着,伸进余热尚在的灶窿里,一面一面的烤。这考验的是耐心,记事时,这项高难工作一般是姥姥完成的(舅舅三年灾害里饿死了,所以姥姥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糍粑烤得两面焦脆,还不破壳跑瓤为最佳。烤好的糍粑可以直接吃,那是香;也可以掰开,往中间加白糖,那叫甜。
最奢侈的吃法——炸着吃。一年中,只有过年时,父亲才会开一次油锅,炸鱼、炸肉之后,也顺便炸几块糍粑。炸过的糍粑金黄金黄的,看着就眼馋。
最耐久的吃法——糍粑果。春节前将糍粑切成薄而窄的小片,在阳光下晒干,收藏起来,想吃的时候,下油锅炸成酥脆的糍粑果。糍粑果的样子与超市的糯米条(荆果条?)相似,只是没有加糖,是纯粮口味的。经过这样一加工,算是零食了,除了自家孩子吃点,还可以用来招待那些来拜年的邻居小孩儿。
最后,糍粑还是礼节食品。春节时,家家户户走亲戚,人来客往的,不一定都在家吃饭,但总得表示下好客的热情,每拔人来了,都得强留下来吃点啥才放行,用妈妈的话说是,大新年的,来家了水也不喝一口就走,是万万不能的。
因为知道天天有客,所以每家都会提前包好饺子,来客人了,开水锅里一下,咕嘟几下就OK,但是,客人来多少的事,咱作不了主啊,饺子也有吃完的时候,现包是来不及了,这时,就由糍粑出来救场了——一碗糍粑煮挂面,再浇上点肉汤,好客之情也照样能表达。
6/三奶奶的“糍粑下挂面”
此时,我又想起了三奶奶的“糍粑下挂面”。三奶奶人生得矮小,听说话的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不知道三爷爷是怎么把她弄到手的,那时是小孩子,也没心思过问长辈们的“艳史”。
三奶奶和我们不一个村,但由于是同族长辈,所以,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村的族叔族兄们都相邀一起去给散住在各村的本家长辈拜年。每年去到三奶奶家,她都忙得没头苍蝇似的,等我们要告辞了,她才想起进厨房,等我们走出老远了,她还倚在门前扯长了声音地喊:“都别走了,我给你们煮糍粑、下挂面吃——”
我们哪有时间回头啊,下一家的饺子正在锅里煮着的呢,再晚就烂了。有不老实的坏小子,也不忘调侃一下三奶奶:“三奶奶,快回屋吧,外面可凉了。今年糍粑煮面就免了,我们明年再来吧!”
现在还想起那时拜年的吃相,还心有余悸:第一家时是狼吞虎咽、第二家是吃半留半、第三家是敷敷衍衍、第四家是胃胀肚圆……一天下来,腿没跑瘸,人却撑傻了。
7/我的糍粑煎鸡蛋
今天的糍粑又宽又厚,买回家后我进行了简单处理,改刀切块,浸入清水中,随吃随取。
改刀时剩下一点边角料,准备做个糍粑鸡蛋。
这样的做法,是受到老妈以前做菜时的启示。那时穷,鸡蛋都有拿去换盐吃了,偶乐来客了,家里鸡蛋不多,做菜的份量不够,妈妈就会从水缸里捞出一小块糍粑,切碎后,和鸡蛋一搅拌,这样,两个鸡蛋就能做出四个鸡蛋的份量来。并且,加了糍粑的鸡蛋,绝对的别出风味,糍糯蛋香,炒菜或煎饼,都是美味。
原来想煎个蛋饼的,只是夜晚怕不好消化,临时又改成炒蛋花了,配碗米粥,呼呼一喝,就饱了。
做法超级简单。糍粑一小块切碎、加入两枚鸡蛋打散,像平时炒鸡蛋一样操作就行。因为要做炒蛋花,我加了点香葱、蒜苗与青椒,一盘零技巧的蛋花糍粑炒时蔬就OK了。
夜深了,梦中的人或许都奔波的回家的路上了吧?年关越近,乡情越怯啊。如果时光能倒流,此生我愿永远生活在豫南的那个六七年代的小村庄。
她的名字,叫“黄围孜”。